下一个十年,一定要让我看见一个更幸福的你
写给亲爱的小来姑娘
小来是我们部门姑娘顾亦来,我习惯叫她小来。
上周二,突然收到她为我特制的我们相识相聚十周年的礼物,坐在办公室发怔了好一会儿,不由感叹:时间过得好快啊!小来大学毕业跟着我居然十年了!可在我的心中,仿佛还像是在昨天,那个戴着大大镜框、却没有镜片,脸还有点婴儿肥的姑娘诚惶诚恐站在我面前向我报到的情景。
“哪里人?”“嘉兴人。”
“哪里毕业的?”“同济大学。”
“到日报综合新闻部很辛苦的,做好吃苦的准备。你,先跑热线开始吧。”
就像把刚学游泳的孩子扔到水里熟悉水性一样,把刚来的大学生放到党报热线这个平台,让他们学会扑腾,这是那时候作为部主任的我常用的办法。
直到若干年后,我才知道那时接听热线的他们,曾经是那么焦灼、那么彷徨、那么痛苦。
“应老师,你知道吗,那时候每天早上最焦虑的是线索,不知道今天到哪儿采访?”
“应老师,当时最担心是写好的稿件被枪毙。我没有休息天,没有节假日,每天疲于奔命,同进报社的大学生每次相聚时,我都因为写稿或者在采访的路上不得不缺席。可那时我的每月奖金只有2000多元时,在分社活儿干得更轻松的却高达4000多元了。”
很惭愧,当时作为部主任的我,根本不知道年轻人的这种焦虑。我只知道不停地拿着鞭子抽打着他们前进。
“今天采访什么?”
“那篇稿件说好的要交了,怎么还不给我?”
“哪里哪里发生啥事,你抓紧去采访!”
……
不管是双休还是节假日,不管他们有没有休息,我总是按照我的节奏催要着我所需要的进程。现在想来,这种管理方式好无情。我不知道小来这十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。我不知道小来他们在背后对我有没有咬牙切齿地骂过:“这个疯老太婆,自己不休息,让我们也没得休息。”不过我知道,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告诉我,很害怕接到我的电话。
今年是我大学毕业工作三十周年。这30年来,我总是不断地在迎来送往中带过一拨又一拨大学生。小来跟我在一个部门相伴十年,算是最长的之一。
在我们报社,在同一个部门,特别是像在我们这种流动性极高的采访部门能够相伴十年,真的十分不容易。报社每两年就要双向竞聘一次,中层干部和员工可以从自己的意愿出发,相互选择自己心仪的归属。小来到报社的十年间,总共经历了5次双选。10年时间里,我一直作为日报综合新闻部主任,小来一直坚定地选择我所在的部门。我们心照不宣,不需要过多的客套与表态。
今年,她曾经向我表达想走的想法。我只需轻轻一句“你不陪应老师啦?”她便泪如雨下:“应老师,我舍不得。我跟别人不一样,我当时是怀着追星般的感情投奔到你所在的部门的。你可曾知道,当年我能在你领导的部门工作,有多开心有多激动吗?”
我不知道我曾经在年轻的小来心中占据着那么重要的地位。我感谢这份尊重,同样会收藏这份尊重。这是满足我此生虚荣心的重要资本啊!
我曾经在很多场合感叹:我只有儿子,没有女儿,但又何其幸运,在部门里碰到那么多姑娘,大学毕业就跟着我,会跟我说或许连母亲都不愿说的知心话,她们都像我的女儿,能容忍我的坏脾气,懂事、贴心,干事麻利,走出去个个都不输男儿。
人的一生,总会把眼前即得的、已经拥有的看成理所当然,不知道加倍珍惜。小来与我相伴的十年间,我很多时候也把它当成必然。直到那天,她跟说:“应老师,十周了,要么我们出去嗨一下?”我才细细回眸:这十年小来有太多的机会选择离开我了!
比如:一开始的“收入太低了!”
后来的“记者活儿实在太累了”!
再后来“想拥有一个更稳定的去处”。
………
小来没有选择离开,而是选择坚守。我感动于她的这份忠诚。
她说:“因为在这个部门我学到了东西。”“熬过刚入职时最艰苦的两年,当我发现我可以写重点稿了,《嘉兴日报》头版头条越来多地出现我的名字了,我的稿件受到市领导批示了,我出去采访越来越受到受该对象的尊重时,职业带给我的荣耀让我找到了奋斗的价值。”
我欣慰,小来在与我十年的相伴中,不是来自某种特殊的庇护,而是通过千锤百炼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。这正是我希望这群年轻人做到的!
我特别担心年轻人在日常中相互对比“哪里活儿轻”,也特别不赞成一些年轻人哪里轻松就变着法儿往儿钻。所以总在部门鼓励年轻人:不要让今天的闲适成为我们进步的阻力。年轻的时候,靠着父母或者拖着三姑六眷的关系挑三拣四,万一有一天这些“关系”远去,你失去了挑挑拣拣的资本,那个时候的你怎么办?千本事万本事,不如自己有本事。这是一个千变万化的社会,只有自己一技傍身,走到哪里都不会发慌。只有靠技能立身,不管世事怎样变化,你才能挺直胸膛活得堂堂正正。
我知道,按照小来的家庭和她自己的能力,她是有“挑”和“拣”的资本的。这十年,她的父母从没有对我说过“关照关照”这几个字,他们对我说得最多的是“对她要求严格一点!”小来自己也无怨无悔地选择留在艰苦的一线锤炼本事。
“艰苦”两字在这里绝不是文人眼里的修饰词。有那么几年时间,《嘉兴日报》微信公号是由我们日报综合新闻部以小来为代表的5个姑娘运行的。那时候,运营微信公号纯属份外工作,报社没给任何奖金,我只能通过向领导争取一些政策,以自筹资金的方式贴补她们的辛苦付出。报酬虽然微薄,但对她们的要求不低,起码的一条是不能遗漏当天发生的重大新闻。很多时候她们白天要采访,晚上做微信。如果发现有突发新闻,哪怕再晚,我一个电话指令,她们即便做好了也得推倒重做。每天早上6点,《嘉兴日报》微信公号必须准时推送跟大家见面。试想一下,一年365天,在每天起早贪黑的坚守中,该有多大的毅力多强的耐力?!因为新媒体语言跟党报语言完全不一样,前者轻松活泼,后来严谨庄重,这就要求小编加速转型。小来曾跟我说:“轮到做微信的那一周,提前一天开始紧张,完全是人格分裂。白天,以党报记者的身份采访,需要严肃且有高度厚度;晚上,当新媒体小编,就像面前站着一群市民,你得用最朴实最有趣的语言,把嘉兴正在发生的大事要事,用最妙趣横生的语言讲给他们听,累是真的累。但我想到自己做了这个以后,今后转型可以走在同行前面,起码人家不会的东西我会了,我不用担心融媒体改革后自己怎么办了,所以我咬着牙坚持做、创新地去做。我们想得最多的是不能丢咱们日报综合新闻部的脸。”
一个小微信公号,让我们凝聚起了强烈的集体荣誉感。这些年来,因为小来她们在每次重特大任务面前,总能无怨无悔、快速高效高质量交出作品,我们所承接的意想不到的任务越来越多。看到把他们忙得团团转,甚至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,我曾经无数次地自责,无数次地问自己:该不该拒绝?值不值得这样做?可是,我总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,无法做到像心里所想的那样,让他们过得不那么忙碌一点。我只能带着满满地亏欠,期待下一个明天会随心所愿。
现在看来,我的梦想会成空想。我只是希望小来他们能懂得,目前所有的忙碌,都是为了更好的成长奠基。我不希望他们在步出大学校门跟着我的有限时间里,由于我的放低要求而松懈了他们本该有追求、荒废了他们最好的岁月。
十年,当年的稚嫩女孩已成长为我倚重的、写重头稿时不可或缺的得力干将。站在十年的门槛上,眺望下一个十年,小来,你一定要让我看见一个更幸福的你!
我不知道我们还会彼此相伴多久,但肯定没有十年的光阴了。我得我为我的优雅老去做准备,一直在蓄势赋能的你则可能迎来人生的骐骥一跃。应老师希望你,不管身处何方、身居何位,继续做那个正直的、善良的、做事麻利、考虑问题周到的你!不管什么都要坚信,凡事用心过、努力过、坚持做,定然有收获。人生犹如一场马拉松,最后的胜利者不是最初跑得最快的那个,而是跑到最后的最远的。每天坚持长跑10公里的你,肯定越跑越会悟到坚持的意义。
著名作家龙应台曾经在《目送》里一文里说: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,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:不必追。”我跟你们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从初出茅庐的新闻菜鸟到日渐成熟的时政记者,顾小来到底经历了什么?我们从有记忆的互联网中,可以窥探一二。

初入职场,飞起来是常态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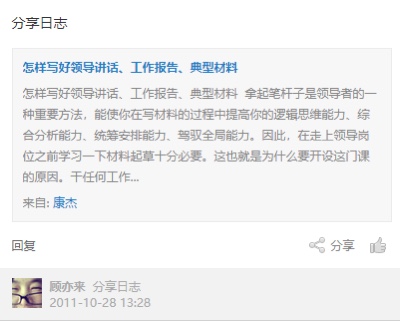
还分享过怎样写好领导讲话......的帖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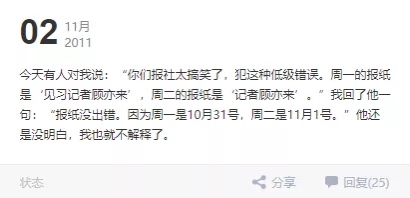
经历了实习三个月,见习三个月,小来终于转正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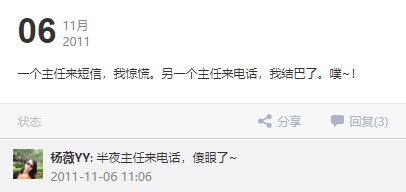
这位杨薇同志是小来的老集美,同一批进报社,目前在同一个部门工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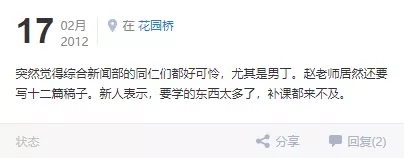
后来,这位赵老师的条线分配给了小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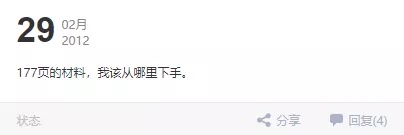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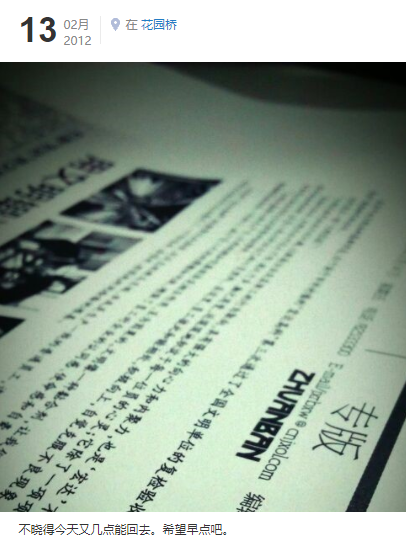
作者:应丽斋 编辑:刘卓文
